當“人才外流”仍被不少人視為“失血”時,任正非的一句話撕開了認知裂縫。2025年12月5日,在ICPC北京總部的座談會上,這位79歲的華為掌舵者面對青年學子和教練,沒有重復“卡脖子”的焦慮,反而拋出一個反常識判斷:“大量人才到美國成長是好事情。”
這話像一顆石子投入輿論深潭。有人質疑“是不是老糊涂了”,有人擔憂“人才都跑了誰來攻關”,但在爭議背后,藏著一個被焦慮遮蔽的真相: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,人才的價值從來不由國界定義,而由其參與創造的文明高度決定。任正非的“反常”,恰恰是穿透短期博弈、直擊長期生存的清醒——真正的科技競爭力,從來不靠“圈養”人才,而靠開放生態里的“共創”能力。
一、人才流動:不是“流失”,是全球培養皿里的“育苗期”

“美國創造的科技文明有益世界進步”,任正非這句話戳破了一個流行誤區:把人才流向發達國家等同于“損失”。但科技史早證明,頂尖人才的成長從來需要最優質的“土壤”。20世紀初,歐洲科學家涌向美國,不是歐洲的“失敗”,而是全球科技中心的自然遷移;今天中國學子赴美深造,本質上是參與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共同體——他們學的不是“美國技術”,而是人類共有的科技文明成果。
華為自身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早期華為研發團隊里,不少人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,這些“海歸”帶回的不僅是技術,更是研發管理的方法論。任正非說“中國多數公司未被制裁仍可用美國技術”,潛臺詞是:技術本身無國界,關鍵在于你有沒有能力吸收、轉化、再創新。如果因為“怕流失”而把人才關在國門內,看似“保住了人”,實則讓他們錯過了接觸最前沿的機會——這不是“保護”,而是“矮化”人才的成長上限。
更重要的是,人才的終極價值是“創造”,而非“歸屬”。一個在硅谷做出突破的中國工程師,他的成果可能被全球企業應用,包括中國公司;一個在波士頓實驗室攻關的華人科學家,他的論文可能啟發北京的科研團隊——這種流動帶來的“知識溢出”,遠比“把人留住”更有價值。任正非的“樂見其成”,本質上是相信:只要中國保持開放,這些在全球成長起來的人才,最終會以各種形式參與到中國科技的進步中——或回國創業,或技術合作,或成果轉化。
焦慮“人才外流”,不如反思:我們能否提供和美國同等水平的創新生態?當中國的實驗室也能誕生諾獎級成果,當中國企業能提供全球頂尖的研發平臺,人才自然會“用腳投票”。任正非的理性,正在于他不糾結“人才去哪”,而專注“回來能做什么”——這才是真正的“人才戰略”,而非情緒性的“人才保衛戰”。
二、開放不是“示弱”,是主動吸收文明養分的“生存本能”

“中國要更開放,吸收世界文明”,這句話從任正非口中說出,帶著沉甸甸的實踐重量。華為被制裁四年,卻依然能維持研發投入增長,靠的不是“閉門造車”,而是“在限制中找開放”——用開源社區合作、國際標準組織參與、跨企業技術聯盟等方式,持續接入全球科技網絡。這種“戴著鐐銬跳舞”的開放,恰恰證明:封閉從來不是“自強”的選項,而是“自困”的死路。
很多人把“開放”理解為“對外妥協”,但任正非的邏輯完全相反:開放是“主動出擊”。就像植物需要陽光雨露才能生長,企業和國家的科技能力,需要吸收全球文明成果才能壯大。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強,強在它能吸納全球的材料、設計、制造人才;德國的精密制造牛,牛在它能整合歐洲的工藝傳統與全球的市場需求。任正非說“吸收世界文明”,不是讓中國“照搬”,而是“消化再創新”——把別人的優勢變成自己的營養,這才是開放的終極目的。
更深刻的是,開放能打破“技術民族主義”的幻覺。近年來,“自主可控”被過度解讀,甚至有人喊出“所有技術都要自己搞”。但任正非清醒:沒有任何國家能壟斷所有技術,即便是美國,也需要全球供應鏈。華為未被制裁的業務能用美國技術,說明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工具,關鍵在于你是否有能力駕馭它、超越它。把“用不用外國技術”和“愛國與否”綁定,本質上是對科技規律的無知——就像當年清朝拒絕鐵路,不是“自強”,而是害怕打破舊體系的脆弱。
任正非的開放觀,藏著一種“文明自信”:不怕別人強,因為相信自己能學得更快、做得更好。這種自信,比喊一萬句“自主創新”更有力量——真正的強大,是敢于承認差距,更敢于通過開放縮小差距。
三、AI落地:不追“星辰大海”,先解“田間地頭”的真問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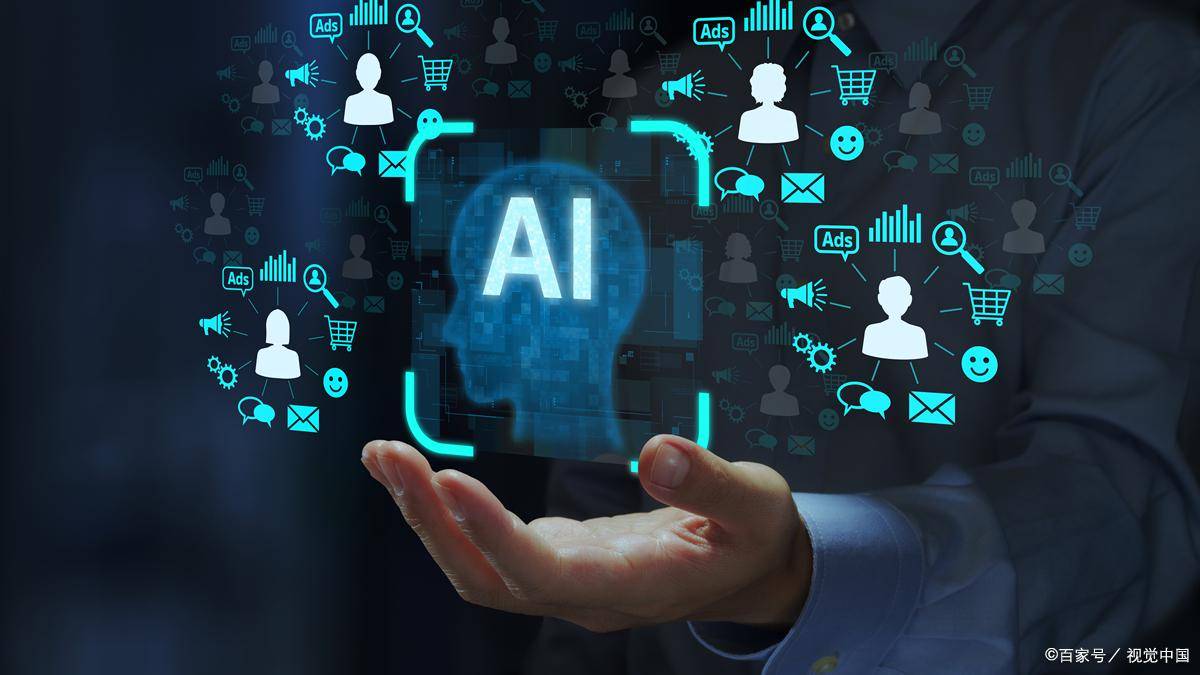
“公司著眼未來3-5年大模型在工農業等領域應用”,任正非這句話,和當下AI圈的“浮夸風”形成鮮明對比。現在不少企業動輒宣稱“要做通用人工智能”,但華為卻把目光投向“工農業”——這個選擇,藏著中國科技企業最缺的“務實主義”。
華為的“務實”,源于對產業痛點的深刻理解。中國是工業大國,但很多工廠仍處于“經驗驅動”階段:老師傅憑手感調參數,質檢員靠肉眼挑瑕疵。AI大模型恰恰能把這些“隱性知識”轉化為“顯性算法”,讓中小微企業也能享受數字化紅利。任正非說“應用”,不是讓華為自己做所有事,而是通過技術賦能,讓更多行業實現升級。這種“利他”思維,比單純追求“AI第一”更有長遠價值——科技的終極使命,是讓復雜的技術變得“可用”,而非讓簡單的問題變得“復雜”。
對比某些企業追逐“通用AI冠軍”的狂熱,任正非的選擇更顯可貴。科技圈從不缺“仰望星空”的夢想家,但缺“低頭拉車”的實干者。當大模型競賽陷入“參數軍備賽”,華為轉向“工農業應用”,本質上是回歸科技的初心:技術是工具,人才是載體,最終都要服務于人的生存與發展。這種“反內卷”的定力,或許才是中國AI真正超越的機會——不是在別人設定的賽道上搶第一,而是開辟解決自己問題的新賽道。
四、教育與企業:各歸其位,才能避免“越界焦慮癥”
“教育與企業目的不同,應避免混淆”,任正非這句話,點破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“責任錯位”。教育的使命是“培養人”,讓人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;企業的使命是“用好人”,讓人才創造商業價值。把企業的“用人需求”直接壓給教育,或讓教育承擔“技術攻關”的責任,都是對兩者邊界的破壞。
現實中,這種“混淆”很常見:高校為了“產學研結合”,過度追逐短期能轉化的應用研究,忽視基礎學科;企業為了“人才儲備”,要求大學開設特定課程,卻不愿投入長期培養。任正非的清醒在于:教育要像“熱帶雨林”,允許各種“奇花異草”生長,哪怕暫時看不到實用價值;企業要像“農田”,專注把“好種子種出好收成”。兩者各司其職,才能形成良性循環——教育提供“人才毛坯”,企業負責“精細加工”,缺了任何一環,都會導致“人才斷層”。
華為的“天才少年”計劃就是這種邊界感的體現:不要求高校培養出“成品人才”,而是通過企業內部的實戰項目,讓有潛力的年輕人快速成長。任正非鼓勵青年“摸高”,本質上也是教育與企業的協同——教育教“底線”,企業給“上限”。這種分工,比喊“校企合作”更有效——教育不越位,企業不缺位,人才才能在各自軌道上最大化價值

